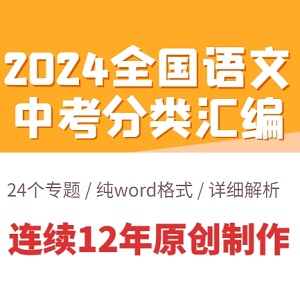约9900字。红楼梦之金陵十二钗 ---林黛玉
林黛玉,林如海与贾敏的独女。因父母先后去世,外祖母怜其孤独,接来荣国府抚养。虽然她是寄人篱下的孤儿,但她生性孤傲,天真率直,和宝玉同为封建的叛逆者,从不劝宝玉走封建的仕宦道路。她蔑视功名权贵,当贾宝玉把北静王所赠的圣上所赐的名贵念珠一串送给她时,她却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这东西!”她和宝玉有著共同理想和志趣,真心相爱,但这一爱情被贾母等人残忍地扼杀了,林黛玉泪尽而逝。
林黛玉,又是一个说腻了却又说不完的话题。
知道《红楼梦》的都知道林黛玉。欣赏《红楼梦》的大都欣赏林黛玉。但200多年以来,人们的欣赏却是多义的流动的。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年纪不同教养甚至不同心态中的读者,其阐释各有各的兴奋点。姑不论“贾府上的焦大”“北极的爱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以及“健全好社会中人”是“不爱林妹妹”也“不会懂得林黛玉型”[①],即使年代与阅历十分相近的人们之间,由于人生遭际审美习惯以及性情心绪的差异,也往往说不到一块去[②]。
这是林黛玉性格的丰厚性所致。
然而,在历代文化人中间,除了共同拥有的怜惜与同情之外,还有同声同气的赞美和冷静客观的推重。后者,又毕竟是一个多数(这里说的多数与历代择偶问卷中的少数甚至“零票”并不抵牾)。
赞美与推重的着眼点,又不能不受到大文化背景的制约。比如从清代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都将林黛玉放到道德文章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精辟精当精彩的论断为证(参见一粟的《红楼梦卷》与郭豫适《红楼梦研究小史》)。本世纪50至70年代,大都将林黛玉放到社会历史天平上衡估,有一系列震撼读者启示后人的论著为证[③]。80年代以后,大开放大包容的氛围促进了思维习惯与研究方法的变革,衡估天平与批评模式的多元化格局开始形成,一系列以深细妥贴的文化透视为特征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现[④]。在多角度多 层面地观照与把握林黛玉性格的浩瀚著述中,以50年代后期出现的“封建叛逆者”说影响最为深远,是近40年间林黛玉阐释中的主旋律。
早在50年代后期,在大学专题课的课堂上,笔者就由衷地接受了何其芳先生的“一对叛逆者”说,尤其喜欢“不幸的结局之不可避免,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逆者,而且因为那是一对叛逆者的恋爱”这一结论,即双重叛逆的双重悲剧说。后来,自己有幸也登上讲台,便把这一掷地有声的结论连同自己趋于简单化的理解连同自己对作品的某些细小体验,热忱地传授给了学生,直到70年代初都不曾犹疑过。
文革中,由于某种特殊因素的激发,重新细读何其芳《论红楼梦》一书,猛然发现,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早在提出叛逆说的同时,就对这一论断作出了极明确极重要的补充:“至于林黛玉的性格特点,如果只用笼统的叛逆者来说明,那就未免更过于简单了。”对此,在以往的听课与读书中竟然忽略了。以此次发现与自省为契机,越来越觉得“如果只用叛逆者来说明”林黛玉性格,的确很难纲举目张地揭开这一不朽典型的全部内涵。换言之,试图以“叛逆者”诠释林黛玉型,动辄会遇到麻烦。退一步说,即便不追求“封建叛逆者”的历史 性内涵,仅仅把她放到与贾宝玉的比较中考察,也不难发现,在价值取向、人际关系、情恋方式等主要方面,她与她的知己之间也有一个不小的距离。甚至有某种质的差异。
首先是价值取向上的距离。
贾宝玉不论对亲权与祖训多么敬畏,他毕竟发表过一些有点大逆不道色彩的言论,还有一些诸如不喜读仕进之书、不搞与仕进有关的社交、不关心家族兴衰荣辱、不打算尽辅国安民责任的行为。
林黛玉如何?小说中从未正面展示过她对类似上述问题的见解,在男人或女人价值取向这个大范畴内,作家没让林黛玉说过什么反传统的或具有逆反心态的话。只有一次,在与贾宝玉的对话中赞赏过探春理家并借题发挥地说:“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看来,她对贾府经济拮据状况远比贾宝玉清醒,对贾府的未来命运也远比贾宝玉关心。只此而已,似不能作为叛逆与否的重要依据。那么,为什么贾宝玉在众多出类拔萃的女儿中偏偏视林黛玉为知 己呢?这是因为,林黛玉从不曾劝谏他去走什么仕途经济学问之路,对他背离传统价值的“无事忙”的人生态度不问不闻听之任之的缘故。和林黛玉在一起,尽管小儿女感情纠葛不断,但在如何做男人这一点上,没有压迫感。她带给他一种宽松空气。在贾宝玉看来,这十分珍贵。对贾宝玉至亲至爱的人们往往是以孟母和乐羊子妻的方式(尽管远不及她们执著)去关心他的,甚至干脆施之以斥责加棍棒政策。在这种“关爱”的背景上,贾母那有原则的呵护,林黛玉那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就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了:
独有林黛玉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等语,所以深敬黛玉。(第三十六回)林姑娘从未说过这些混账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账话,我早和他生分了(第三十二回)
以上两处文字,正是“共同叛逆说”的事实依据。
然而,还有另外一些事实。有必要从事实的全部总和和事实的相互联系中一并思索。比如第九回,宝玉为与秦钟亲近而重入家塾时曾特意向黛玉道别。黛玉听宝玉说上学去,因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从黛玉的口吻看,她的这番话是有不确定性的,既可理解为善意的调侃,也可理解为亦庄亦谐的祝愿,因此不必过于认真。但黛玉毕竟把上学读书与蟾宫折桂挂上了钩,这不能不启发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假如贾宝玉此去,果真或半真半假地寒窗苦读起来,果真或游戏人生似地弄个举人进士当当,林黛玉就由此与他貌合 神离分道扬镳了吗?细读全书与全人,似读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