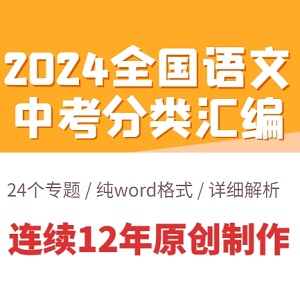约8400字。食指论
□陈 超
《新华文摘》2007年第17期
凛冽的暴风雪中冻僵的手指扳动着
车轮的辐条,移动着历史的轮胎
大汗淋漓,耗尽青春的年华
前进的距离却是寸寸相挨
抬头风雪漫漫,脚下白雪皑皑
小风吹过,哆嗦得叫你说不出话来
可要生存就在苦寒中继续抗争
这就是孕育着精神的冰和雪的年代
人生就是场冷酷的暴风雪
我从冰天雪地中走来
这是食指《暴风雪》中的诗句。每当读到它,我的心总是“咣”的一声,出现一辆风雪中的独轮车的形象,它如此准确地命名了诗人的命运和诗路的辙迹。而且,在我心里它还时常会与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诗人》中的句子发生叠印:“诗人孤独地生活/沼泽地里巨大的独轮车。”而无论是天寒地冻还是淫雨泥泞,推车人的命运都是惨烈的,但他留下的弯曲辙迹,却更深地捺进了时代和人心。 一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得不以“民间”(地下刊物)的方式,在极为有限的小圈子内传播。郭世英、张鹤慈及其“X小组”、张郎郎等人及其“太阳纵队”,包括诗人黄翔、哑默及其“野鸭塘沙龙”,当时其作品从意蕴到艺术成色,尽管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由于乍起便遭劫难的命运,它们对诗坛和读者群的影响毕竟是极为有限的。而真正使这种忠实于心灵,忠实于艺术本身,独抒情志,追寻现代诗本体依据的作品,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乃至更新一代文学青年情感的诗人,还应该说是后期“太阳纵队”的边缘人物——诗人食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真正、也是唯一带着作品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的诗人”。
张郎郎在《“太阳纵队”传说》一文中说:“郭路生(食指)来找我参加‘幸存者诗歌艺术节’,用食指点着我说:‘别客气了,我那首《相信未来》,题目得自于你。’那首名作,我在大狱里听说过。70年代,在地下隆隆地轰鸣过一段。白洋淀的好汉们,都读过。有人说,那是一种火种的传递。那四个字,就算是我先说的,又算得了什么?真正的力量在于他的诗本身,他的诚挚,他的敏感,他的激情。那时我听他念了那首关于鱼的诗,关于在浮冰上的那条鱼(即《鱼儿三部曲》,写一条坚冰下游动的鱼儿,为寻找阳光而跃出冰排后惨死的寓言。——引者注)。至今,他还是当年那样,他是那个时期的一条鱼。我们是某种鱼出现的前奏。”
张郎郎的表述尽管简略,但非常中肯而准确。“火种的传递”,道出了食指诗歌与此前地下诗歌休戚相关的精神血缘;“浮冰上的鱼”,道出了食指诗歌已跃出高寒惨烈而遮蔽的冰面,向更多的人显赫呈现(“隆隆地轰鸣过一段”);而“我们是某种鱼出现的前奏”,则形象地昭示“我们”(“X小组”、“太阳纵队”)尚未跃出冰面就横死于坚冰下的水流中,坚冰下的“前奏”,引出了坚冰上的“正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