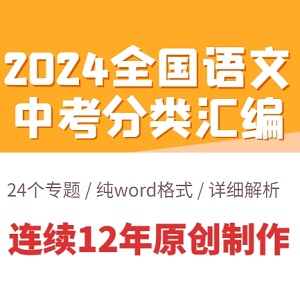共10篇,约11000字。
红 枣 熟 了
佚 名
红枣熟了。
山东灵宝大枣,个大味甜,清脆爽口。价钱也不便宜。
贩枣子的都知道,这时节去灵宝,要带上大把的钞票,赔上晚上的好觉,在枣子的海洋里争夺,眼睛红得跟枣子一般还不能歇息,这才能把满车的枣子给运出去,换成更多的钞票,换成老婆手上脖子上的金戒指金项链,换成娃娃的新衣裳新玩具,换成自己的小酒好菜,然后洗个滚烫的热水澡,哄着孩子抱着玩具睡了!
辛苦,但也值了!
只有柴米不这么干。那么多人,赶着这时节去抢生意,累个半死才换了几个钱?做生意靠的是脑子!
他总是等枣子晒干了,去那个小小的山村,那里也有上好的枣子。因为那里没路,运不出来,所以只能指望着几个行脚的货郎用廉价的日用品去换。
一筐上好的枣子才换个油盐酱醋,换个针头线脑!
货郎没本钱,可柴米有。
等的那些山村的小伙子大姑娘都着急了,柴米才去山村,多少给几个现钱,也就把枣子给全包了。再花上几个钱,让人给挑出山,倒在等候在公路边的小货车里,那就是钱啊!大把的钱!
旁人不知道这地方,柴米谁也不告诉,连老婆都不告诉。有人争抢,这生意就不好做了。
10多年了,就靠这生意,柴米家盖了3层小洋楼,小县城里独一份!
估摸着日子也差不多了,柴米出门,叫上小货车。
贩枣子的旺季过了,运输生意也不好,都争抢着拉活儿,价钱也就便宜。小钱也是钱,这道理柴米懂!
七弯八拐,上坡下岭……柴米让车停在公路尽头,自己上了山。山路崎岖,走了大半天才看见山村的轮廓。
一筐筐的红枣都装好了,就等柴米来收了,柴米扒拉开计算器,过秤给钱。也有那住得远的,拿个小筐送来,柴米也就随便给上几个,人都说柴米仁义!
收罢了,也叫上了棒小伙子,赶早出山,还能赶在明天天亮前把枣子送到县城。柴米也收了包袱,点上香烟,等那些棒小伙子回家取来干粮衣裳就出发。
货都上了肩了,那个老太太却来了,还提着筐枣子,一步一挪的。
柴米认得那老太太,就住山腰的茅草房子,那房子都快塌了,几根木桩撑着。都十来年了,每年柴米进山都见着,她每次都是拿着一小筐枣子换钱,一块两块、三块五块的。就是一年比一年来得晚了!
收了比往年多的枣子,柴米高兴,抓过了小筐,扔下5块钱,转身要走。
老太太拉住了柴米,哆嗦着说话:“今年这枣子不要你钱,求你个事呐,带上我出山啊!”
柴米犹豫了,一老太太出山,脚力跟得上么?
这时来了个棒小伙子,挑了副扁担箩筐,一头是半筐湿劈柴,一头是棉絮被褥:“我挑着老太太出山吧,求你给他指个路,老太太要出远门啊!”
柴米也就不多说了,带上老太太走了。
出山了,老太太上了小货车,抱着个小包袱,闭着眼睛不敢看窗外,说是眼晕。
夜路难走,烟也抽完了,柴米给老太太拉话:“出门呐?上哪啊?”
老太太还是闭着眼:“上个老远的地方,比县城远呐!云南……”
柴米打了会瞌睡,又问:“去云南干啥呀?”
老太太抱着包袱:“看俺儿啊……给儿带上的煎饼、大枣,我儿最喜欢这个!”
天亮了,车也到了县城,老太太哆嗦着拿了个纸片问柴米:“这是个啥地方?有车能去不?”
柴米看看,愣住了。那纸片子上写的是———“云南麻栗坡烈士陵园”!
柴米小心加小心地问:“老太太,你儿子?”
老太太递过一叠钞票,一块、两块、五块的,“没了!早没了!就埋在云南了。老早想去看看,可没钱呐,卖了10年的枣子,俺寻思够个车票了。烦劳你给买个票啊,我不认得几个字的……”
柴米哆嗦了,跟筛糠似的哆嗦!
他把老太太扶上车,直奔济南!小县城,哪来的火车啊?
送老太太上了车,找了个乘务员说了,还给乘务员送上条好烟。乘务员黑了脸,哆嗦着把烟扔给了柴米:“收了你这烟,我还是个人呐?”
老太太只有三五十块钱,火车票哪里止这个数?那钱被柴米塞到了老太太的包袱里,还添上了几张。
回来的路上,柴米黑了脸不吭声。到家了,柴米喝了一夜的闷酒,狠狠抽自己:“咱也是个人啊!”
天亮,柴米揣上票子,买了水泥木料,请了高手瓦匠……
进山!
——摘自《羊城晚报》2005/04/16
学无止境
这是美国东部一所大学期终考试的最后一天。在教学楼的台阶上,一群工程学高年级的学生挤做一团,正在讨论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的考试,他们的脸上充满了自信。这是他们参加毕业典礼和工作之前的最后一次测验了。
一些人在谈论他们现在已经找到的工作;另一些人则谈论他们将会得到的工作。带着经过四年的大学学习所获得的自信,他们感觉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并且能够征服整个世界。
他们知道,这场即将到来的测验将会很快结束,因为教授说过,他们可以带他们想带的任何书或笔记。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他们不能在测验的时候交头接耳。
他们兴高采烈地冲进教室。教授把试卷分发下去。当学生们注意到只有五道评论类型的问题时,脸上的笑容更加扩大了。
三个小时过去了,教授开始收试卷。学生们看起来不再自信了,他们的脸上是一种恐惧的表情。没有一个人说话,教授手里拿着试卷,面对着整个班级。
他俯视着眼前那一张张焦急的面孔,然后问道:“完成五道题目的有多少人?”
没有一只手举起来。
“完成四道题的有多少?”
仍然没有人举手。
“三道题?两道题?”
学生们开始有些不安,在座位上扭来扭去。
“那一道题呢?当然有人完成一道题的。”
但是整个教室仍然很沉默。教授放下试卷,“这正是我期望得到的结果。”他说。
“我只想要给你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使你们已经完成了四年的工程学习,关于这个科目仍然有很多的东西你们还不知道。这些你们不能回答的问题是与每天的普通生活实践相联系的。”然后他微笑着补充道:“你们都会通过这个课程,但是记住——即使你们现在已是大学毕业生了,你们的教育仍然还只是刚刚开始。”
随着时间的流逝,教授的名字已经被遗忘了,但是他教的这堂课却没有被遗忘。
囚绿记
陆蠡
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
我住在北平的一家公寓里。我占据着高广不过一丈的小房间,砖铺的潮湿的地面,纸糊的墙壁和天花板,两扇木格子嵌玻璃的窗,窗上有很灵巧的纸卷帘,这在南方是少见的。
窗是朝东的。北方的夏季天亮得快,早晨5点钟左右太阳便照进我的小屋,把可畏的光线射个满室,直到11点半才退出,令人感到炎热。这公寓里